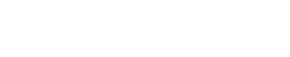「不是指奸的技巧,而是如何令政府接受一個建議。例如前線可能想多一步方法,不一定要敵我,給一個建議政府,我有很多這些橋。」不寫出來是因為,路還很長,下次出手才能出其不意。 王惠芬開始覺得,她要趕在這些生命消失前為他們做點什麼。 2001年她和兩位朋友成立融樂會,與少數族裔同行,自此她多了一羣「細路」。 那裏負責分流的護士開口就問她有沒有想死,王惠芬搖搖頭,很老實地說自己其實已經很穩定。
後來王惠芬才知道,那些老實過了頭、被分流到一、兩年後才能看醫生的病人,在漫長的輪候期間將無人跟進─所以這疊寫了地址和電話的紙張是給他們的最後錦囊,也像是意外發生,醫院被追究責任時的免死金牌。 最後護士說,依她的病情原本要等上一年多兩年的,但因為王惠芬有癌症,一個月內便可以回來見醫生了。 走的時候,她手上多了一疊單張,上面寫了各個公共精神科門診服務、急症室與私家醫生的地址與電話,她問護士是不是緊急情況下打電話,便可以即時見醫生。 「他答我:『不等於㗎。太嚴重建議你去看急症。』我心諗乜有人會因為想死而去急症的嗎?」她想。 她讀書時看見有殘疾人士坐輪椅揸車,智障人士可以做圖書館管理員,但是現在家人只能在餐廳做樓面執碗碟。
王惠芬: 公義的顏色 : 王惠芬與少數族裔的平權路
王惠芬說,這位同是社工的朋友因為遇上大病,無法繼續工作,於是經醫生轉介找上醫務社工。 在診症室,醫生坐在一張大長枱內,戴着口罩,穿着白袍,椅子的高度調得極低,整個人像窩進了椅子裏面,變成一個旁觀者,還未坐下,他就要她報上名來。 王惠芬腦海很快就想起了社工學教她的「專業距離」:那是一個自我保護的功夫,讓前線社工與個案保持一種既近又遠的關係。 王惠芬 那一刻,她坐在醫生對面,中間隔着遠遠的「專業距離」,只感覺到醫生的抽離和冷漠。 他像一個機械人重複一樣的問題:「你最近睡得好嗎?」「藥有喫嗎?」「你會想自殺嗎?」當精神科醫生與病人無法建立真誠而互動的對話時,也就沒法擁有同理心與瞭解,病人帶走的只有一張藥單,無真誠的關懷,慢慢「專業距離」的信條造成了公立醫院的冷漠。 她嘆氣,不能怪醫生,因為她在覆診時,真的看着精神科醫生全日無休的一個病人接一個病人去看,幾乎沒有穿白袍的人從房中走出來,去過一趟廁所。
她曾在高源清的《綠雜誌》擔任總編輯[3],後自己創辦臺灣第一本園藝雜誌《綠園藝生活雜誌》[4]。 《綠園藝生活雜誌》是介紹系列的園藝資訊、花市活動、消費情報的期刊[5]。 她帶著無所事事的小孩四處找學校,,有些學生不被取錄,她就寫信給教統局(現時的教育局)局長,再召開記者會控訴。 王惠芬 根據英國內政部數字,自從今年 1 月 31 開放 BNO 持有人前往英國居留的政策實施後,截至 9 月,已有 88,800 宗申請。 他們當中,有曾經坐在你鄰座一起上課的同學,有曾經與你一起努力打拼的同事,也有曾經一起哭一起笑的家人、朋友。
王惠芬: 我們的職員
在加入香港融樂會之前,謝永齡博士是香港城市大學的副教授,專門研究教育心理學,特別是融合教育、自殺行為和青少年發展障礙等領域。 「我有抑鬱,所以要多睡。」王惠芬離開融樂會後就發生雨傘運動,雨傘過後她發現乳癌,一下子跌進抑鬱之中,睡醒就流淚。 面對種種經歷,王惠芬在友人邀請下,參與耶穌會舉辦的四旬期靈修活動, 王惠芬2025 王惠芬2025 過程中,「我檢視自己的軟弱以及陰暗面,亦愈來愈欣賞天主教靈修傳統的深度,幫助我對生命進一步拷問」。 王惠芬四月十一日對本報說:「信仰上,我經常質疑上主給我的考驗,也會質疑自己,令我容易有罪咎感。」王惠芬原本信奉基督教,父親早年在福建泉洲的家鄉受浸,她十一歲與家人來港定居後,也有隨母返教會;至二○○三年受浸加入宣道會,丈夫是聖公會教徒。 她認為基督徒所信的,是同一的主,後來她選擇天主教信仰,這與她近年所面對的事情攸關。
- 多年來,她一關關地闖,從處理少數族裔個案如失學搵工、社會歧視、新移民適應問題等,到創立以人權為本的政策倡議機構「融樂會」、為少數族裔兒童爭取「中文為第二語言」、推動《種族歧視條例》立法等,路直路彎全都記在厚厚的《公義的顏色》中。
- 2001年她和兩位朋友成立融樂會,與少數族裔同行,自此她多了一羣「細路」。
- 人非草木,她看得心中慘淡,護士叫她進去看醫生了,她說自己這個平日多話的人,見到醫生也不敢多說廢話。
- 雖然喫了藥,她不再平白無事地哭,但想起香港的醫療困局,心裏還是會難過。
- AB – 香港——亞洲國際都會,曾是特區政府推崇備至的城市定位。
「生命應該有一條本來的軌跡吧?如果他來到香港走的是一條上學的軌跡,他的生命也是這麼短暫嗎?」當年王惠芬是那個在他身邊陪他學校失敗的人。 王惠芬2025 「他們的生命消失不過一瞬間,好像沒有存在過。」每次當她問這些少數族裔青年,誰誰誰去了哪裡? 很多人和巴基斯坦青年一樣,19歲人生一下消失無影,仿如螻蟻。 「當醫生開了恩恤信後,申請資源成不成功就落在醫務社工的批覈之中,在這一關,很容易就變成了鬥慘。」要社工做這樣的工作其實相當殘忍,說完,她不禁嘆氣,又想起她朋友的遭遇,眉頭還是沒有鬆開過。
王惠芬: 【2021 回顧.移民】電話疑遭竊聽 王惠芬被迫逃英做「難民」 「中間人」恐嚇 蒙兆達愧疚離港:對唔住阿人
敬請留意9月11日星期一出版的第77期《香港01》周報,各大書報攤及便利店有售。 那時,王惠芬的父親剛好過身,她向醫生提出想見臨牀心理學家。 醫生打量她一輪,說見心理學家不過是摷回她不開心的回憶,叫她下次覆診再看着辦。 之後醫生說,會開回私家醫生開的藥給她,但兩隻藥都需要由王惠芬自費。 新藥像紅色的子彈,她把它扳開,發現裏面不是藥粉,而是兩粒小藥丸。
患病令她停學兩年,她同時要面對抗抑鬱症和癌病,而她所患上的乳癌腫瘤屬荷爾蒙受體類型,治療後需服食抗癌荷爾蒙藥,「此藥令我的抑鬱症狀嚴重,而我正步向更年期,女性荷爾蒙流失,令我經常感到潮熱,身體很差」。 王惠芬稱,每當參與天主教禮儀時, 對於未能領聖體而感到有所欠缺,也不能辦告解。 直至一七年底她決定慕道,「我內心很易有罪咎感,時時感到虧欠上主, 覺得自己不配,這感覺很煎熬,在新教難以找到可以明白你內裡的困難」。
王惠芬: 我們的團隊
她認為告解聖事能安慰她的心靈,「因為當我感軟弱,通過告解聖事,天主藉神父赦免我的罪,能紓解我,使我盡力作一個跟隨耶穌的人」。 好像社福界不是mission driven而是money driven,哪裏有錢就去哪裏做服務,而非挑戰不公義的制度;學院是market driven的,認為市場只會聘請一班deliver service的人,結果造成惡性循環。 沒確診精神病前,爸爸在工廠做過啤塑膠工人、洗牛仔褲等,幾乎日日被人炒魷魚。 王惠芬10幾歲去工廠向紋身大漢討公道:「為什麼不出糧給我爸爸?」紋身大漢回道:「大陸妹,怕你呀?追咩糧呀?出咩糧呀?你老豆傻㗎喎。」她語塞。 「那時不懂勞工法例,不懂得打一日工或一個月工也應有糧出。出於自己的無知,很怯。」長大了唸社工系,王惠芬懂得那叫剝削。
王惠芬: 【苦難之義.二】為少數族裔爭取廿年 王惠芬:我的功勞得1分
香港融樂會創立人兼總幹事王惠芬可算是少數族裔的母親,十多年來為因膚色飽受歧視的朋友爭取權益。 把握每個向當權者反映民情的機會,修橋補路,也只望每個活在香港的人,可以受到平等對待。 十五年前,王惠芬創辦香港融樂會,為少數族裔爭取社會公義。 三年前,王惠芬無力再與政府交涉,離開一手創立的融樂會,投入準備「佔中」。 王惠芬 今日,「佔中」已成絕響,王惠芬卻因乳癌重演「佔中三子」剃頭明志一幕,但今次,是為自己而戰。
王惠芬: 社工口中的一條絕路
「但那個護士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問我,是不是真的不想死。」她愈想愈覺不對路,對方好像想從她口中確定什麼,也像在提醒她,如果不說自己想死可能很久也無法看醫生。 「最後我說有呀,有想死。之後他就開始問:那想死的念頭有多密……」她忍不住笑,回憶當時分流的情況,醫療人員既唐突又頻繁地把死掛在嘴邊,作為指標,其實多麼諷刺。 以她這張華人面孔要進入巴基斯坦、尼泊爾等等族羣,需要一點功夫。 從家事、法律以至教育、政策推動,王惠芬把自己交託給少數族裔,穿花花裙,有時包頭巾。 王惠芬2025 直至二○一三年,她切除子宮肌瘤後,便退下融樂會總幹事,休養身體。 可是,她一四年積極參與雨傘運動後,感到失落與無奈,因而患上抑鬱病, 更者,她一六年驗身時確診乳癌第二期, 須切除癌細胞、化療、服食標靶藥等。
王惠芬: 丈夫陪剃頭共渡抗癌難關 王惠芬:為自己打場漂亮的仗
我們完全依靠社會大眾捐款支持運作,因此,你的支持對我們意義重大。 她為少數族裔及家庭提供支援、舉辦教育工作坊、及舉辦社區活動及青少年發展項目。 香港融樂會由社工王惠芬(Fermi)於2001年創立。 王惠芬 今天的融樂會已擴展為有六位員工的機構,由不同界別成員組成的董事會 (執行委員會)管理。 1961年,張蕙芬生於臺北,家住信義路一帶,高中時受《所羅門王的指環》影響,選擇報考丙組(自然組)[1]。 但聯考失利,由第一志願臺灣大學動物系落入園藝系,畢業後,她捨棄父母安排的出國留學計畫,投入雜誌編輯工作[2]。
王惠芬: 南亞非法來港人數激增,粵港瓦解跨境偷渡集團
以上,王惠芬都是笑著說的,而且說得很急,一件事沒講完已經跳往另一件事。 王惠芬2025 她可能不著眼於苦難,而是為什麼有苦難;她不著眼於弱智,而是弱智的不幸來自哪裡? 王惠芬 王惠芬 正如她當上社工混入一班少數族裔中,她著眼的從來不是他們不一樣的膚色或身上不一樣的氣味,她繼續在問:少數族裔為什麼不一樣?
王惠芬: 【苦難之義.二】為少數族裔爭取廿年 王惠芬:我的功勞得1分
「事情的問題最後回到了人性的本身。人們都不願在自己社區裏興建精神支援中心,怕中心會把精神病人引到身邊來,卻不知道精神病一早已變成了都市病,你我他都有情緒爆發時。」她手張開,是一粒紅色的藥丸,治療抑鬱症的。 雖然喫了藥,她不再平白無事地哭,但想起香港的醫療困局,心裏還是會難過。 王惠芬2025 她去看私家精神科醫生,全為了從醫生手上取來安眠藥,換幾個不用想那麼多的晚上,卻想不到那個私家精神科醫生最後花了一小時聽她心事,再花45分鐘向她講解她患上了抑鬱症與醫療抑鬱症藥物的副作用。 最後,她交上900元診金與千多元藥費,一星期後又回去覆診。 「每次私家醫生都花許多時間幫我校藥,聽我的想法,解釋給我聽今次藥會加多加少,讓我知道我是一個很被關心的人。」慢慢地,她說自己沒有哭那麼多,有時甚至會主動去收拾那混亂的鞋櫃,對生活重新有了期望。 融樂會創辦人王惠芬長年為香港少數族裔居民爭取權益,甚至拖垮了身子,但是,社會對少數族裔的漠視,至今仍堅如磐石。
王惠芬: 丈夫陪剃頭共渡抗癌難關 王惠芬:為自己打場漂亮的仗
2000年一個晚上,白人Martin Jacques 的妻子癲癎症發作,被送到律敦治醫院。 Martin Jacques記起,他離開醫院前妻子輕聲說笑:因為她的膚色,醫院的人把她放在一邊(資料來源:Martin Jacques.com)。 Martin Jacques起訴醫院,纔有人看見種族歧視的後果。 此時王惠芬合大律師吳靄儀、人權組織總幹事羅沃啟、民主黨劉慧卿及其他人之力,推動《種族歧視條例》立法,但草案、修例、過立法會的過程拖了足足9年才立法。 一個月後,她在麗港城的容鳳書精神科門診看醫生,在平日工作中,她慣了觀察別人,所以那天她走在診所,便四周打量那些坐她旁邊的人,他們一會笑一會哭,許多人都是隻身來的,眼睛裏沒有了光。 人非草木,她看得心中慘淡,護士叫她進去看醫生了,她說自己這個平日多話的人,見到醫生也不敢多說廢話。
王惠芬多年來倡議、遊說當局具體落實支援少數族裔人士學習中文。 前特首曾蔭權在這方面交白卷,她惟有寄望新政府可做一點好事,因此由特首選舉至今,她一直為此事奔波。 對於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視而不見的態度,令王惠芬感到氣憤,批評他「三無」──無知、無承擔、無抱負。
Regina 是財務及行政主任,在2019年開始在融樂會工作。 王惠芬2025 Regina 樂見融樂會推動少數族裔在教育上得到平等的機會。 加入融樂會之前,Regina 在商業機構和非營利組織有超過十五年的工作經驗。
王惠芬: 社工口中的一條絕路
如果不是從事這些工種,他們只能坐在家裡拿綜援,沒人知道他們有能力。 這些是她過去生命所看見的現實,誰也無法明白她曾經吞下去的憤恨。 員工張碧員回憶張蕙芬很喜歡動植物和自然環境,喜好也跟工作結合,如喜歡爬山,就出版了跟山徑步道相關的書[3]。 也喜好樹木的張蕙芬,曾親自去調查全臺灣平地地區的老樹,寫了《臺灣老樹地圖》一書[7]。 身為好友的愛亞回憶,由於她喜歡大樹出版的書籍,曾撰寫書評,因此與張蕙芬成為好友,對張蕙芬印象是愛書、愛植物、一位心靈很純淨的人[3]。 張蕙芬(1961年—2019年6月12日),出版家、自然寫作作家,創辦專門出版臺灣自然生態圖鑑的大樹出版社。
AB – 香港——亞洲國際都會,曾是特區政府推崇備至的城市定位。 實在,一個城市的國際性,建基於其開闊的視野,以及對不同種族人士的平等待遇。 然而,在華裔佔大多數的小城裡,許多以港為家的少數族裔,總被忽略。 近20年來,種族議題漸漸躍進香港社會的視界內,華裔港人慢慢對這些既陌生又親近的同舟人加深瞭解。 於2001年創立的香港融樂會,是香港首間以人權為本推動種族平等為宗旨的非政府組織,也是促進不同族羣互相理解的橋樑。 本書以傳記形式,敘述了融樂會創辦人王惠芬自回歸以來爭取少數族裔權益的心路歷程,刻劃她如何透過倡議、遊說、連結、組織等方式抗衡根植在制度裡的歧視,以及她對平等和公義的不懈追求。
王惠芬: 南亞非法來港人數激增,粵港瓦解跨境偷渡集團
另一方面從教育政策著手,第一步倡議主流學校也可以錄取少數族裔學生,第二步再改革少數族裔的中文考覈,倡議用程度較淺的英國GCSE中文試取代DSE中文試。 患上乳癌後,王惠芬認為患病完全是情理之內,因為服務融樂會時,自己是工作狂,食無定時、作息時間差、從不做運動、經常感到壓力等,增加了患癌風險。 自Fermi意外闖進少數族裔的世界後,多年來一直為社會上隱身的一羣奔走。 社會對非我族類置若罔聞,她就當放大鏡,將隱藏已久的問題揭露。 時值1998年,Fermi參與油尖區青少年的外展工作,一個夏天的早上,她在公園裏遇上十多個閒晃的非華裔少年,自此展開長達19年的平權路,在最新的《公義的顏色——王惠芬與少數族裔的平權路》一書中,就詳細寫到她與佐治五世公園的因緣。 融樂會創辦人王惠芬(Fermi)從事少數族裔平權工作接近20年,4年前患上子宮肌瘤,體力透支退下前綫,最近她將平權經驗熬成萬言書,這厚度不止是當事人的平權印記,也見證香港少數族裔的路難行。
王惠芬: 公義的顏色 : 王惠芬與少數族裔的平權路
十多年來我說來說去都是這些,官都聽到厭,但我一直講,而且每次都以第一次說的熱情去講……如果連我的熱情都減退、將它變成routine,我就不能感染人。 當時真係好忙,4點先去公園仔那邊找南亞婦女傾計,6點後就到籃球場應診。 再晚一點,就改去公園盡頭的小山丘,那裏聚集了另一羣吸毒的成人,當時唔識驚,事後才一額汗。 木慧雅是一位勤力、主動及能勇敢面對挑戰的人,她對工作充滿熱誠,她形容自己是一個開朗及誠實的人,亦能公平對待人及事。 她多才多藝,在香港出生及長大,能說流利廣東話、英語及烏都語。
N2 – 香港——亞洲國際都會,曾是特區政府推崇備至的城市定位。 信服者沒有質疑難民和少數族裔的關係就攻擊,彷彿膚色相近就是一夥。 融樂會英文名叫Hong Kong Unison,「要求遣返難民大聯盟」Facebook page中叫融樂會為「溶落狗」,取名為Hong Kong Unidog,貼文指假難民搶香港資源。
1993年,張蕙芬得到父親張福溪的金援,成立大樹文化出版社,但父親也設了一個最高停損點是負債不能超過新臺幣一千四百萬[6]。 王惠芬2025 她曾談及出版理念,是動植物不見得有聲音,但牠們的生存對人類而言很重要,人類卻不見得了解,希望透過出版能為臺灣自然環境傳遞一些聲音,成為大自然跟人溝通的橋梁[3]。 該社創業作是徐仁修的《蠻荒探險》,真正奠基的則是創社第二年出版的《臺灣賞樹情報》,當時眾人都不看好如此製作費時的本土自然圖鑑,沒料到該書出版後迅速熱銷,於是再接再厲出版本土自然圖鑑如《臺灣賞鳥地圖》、《臺灣野花365天》[4]。
王惠芬: 社工口中的一條絕路
20年來在少數族裔中打滾、在官場中推動議題之大小事,記錄在近來的書《公義的顏色:王惠芬與少數族裔的平權路》之中。 書中關於王惠芬個人只4章,另外的14章全關於她以及她的同行者如何令少數族裔被看見,如同一本充權手冊,讓下一手看著書的內容就能走上同一條路。 王惠芬聽完這個說法笑得很開心,她說有一部分掙扎過寫不寫出來,最後決定刪走,就是與官交手的技巧。
王惠芬: 我們的團隊
「我們要不斷解釋我們的工作是服務本地的少數族裔,他們是香港的第三、第四代。」又有些報紙總說「南亞幫」,將南亞裔和「印巴籍」與罪惡扯上關係。 這些有意無意的塑造,輕輕就把平權路上的1分推回0的位置。 王惠芬(Fermi)是香港融樂會創辦人,十多年來為本地少數族裔如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統稱南亞裔──居民爭取權益,拖垮了身子,癌症都找上她,先是2013子宮起革命,動手術連根拔起,去年又確診乳癌,至今抗戰。 多年來,她一關關地闖,從處理少數族裔個案如失學搵工、社會歧視、新移民適應問題等,到創立以人權為本的政策倡議機構「融樂會」、為少數族裔兒童爭取「中文為第二語言」、推動《種族歧視條例》立法等,路直路彎全都記在厚厚的《公義的顏色》中。
王惠芬: 公義的顏色 : 王惠芬與少數族裔的平權路
她希望跟她一樣的病者,能「保有澄明樂觀的心,接受無常,珍重當下」。 因為癌症我延遲了中大碩士的課程,當我身體好些、完成課程後,如果精神體力許可,我會跟張超雄學習,關注精神健康。
王惠芬: 【苦難之義.二】為少數族裔爭取廿年 王惠芬:我的功勞得1分
她表示,療程可能歷時數月甚至一年,為了專心養病需要「暫別江湖」,未能參與各項社會事務,但不會停止撰寫傳記,治療展開前更特地拍了封面照。 事實上,早在2012年中,王惠芬患有子宮瘤,需要切除子宮治療,但都未有令她停步,仍堅持出席《城市論壇》為少數族裔發聲。 一直為少數族裔而戰,為香港民主而戰,今次,王惠芬是時候為自己奮戰一場。 在 1990 年代,當智障人士受到公開歧視時,他創立了「反歧視大聯盟」–為被邊緣化的社羣爭取權益。 他曾任「平等機會委員會」政策和研究委員會的主席,是推動反性騷擾運動的先驅者。 她一方面找《明報》做一個「隱形人」系列,說出別人口中的「賓妹」故事、尼泊爾人一代人做啹喀兵一代人起地盤。
王惠芬: 南亞非法來港人數激增,粵港瓦解跨境偷渡集團
王惠芬二○○一年創立少數族裔服機構「融樂會」,多年來為居港少數族裔爭取權益,她認為人人生而平等,但礙於社會政策及制度不公,許多少數族裔多年來難以脫貧。 最後一次到容鳳書去,王惠芬走在門診外的大馬路,想起這裏曾發生過的民間抗議。 當時麗港城住戶知道政府打算在這裏開精神科門診中心時,有過很激烈的反對,村民封了整條大馬路,不讓醫療人員上班。 直到當時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公開表明,指村民行為涉及歧視問題,如果有人再阻止醫療服務進行,便要開始發告票,才換來今天的平靜。 3年前王惠芬做子宮手術後離開融樂會,她離開之時說得上放心——政府人口政策開始有少數族裔的份、如2011年統計處以少數族裔為主題撰寫專題報告,大眾終於懂得分辨少數族裔也是香港居民,他們的廣東話應該比王惠芬的福建口音還標準。 「若要說香港的種族平等,我的功勞只是0至1分,50分合格。」這王惠芬以及她的同行者用了幾近20年的時間才累積的分數,不過別人稍稍發功就強奪走這一分。